《前线》刊发历史研究所刘仲华研究员理论文章《从北京看中华文明包容性》
从北京看中华文明包容性

原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25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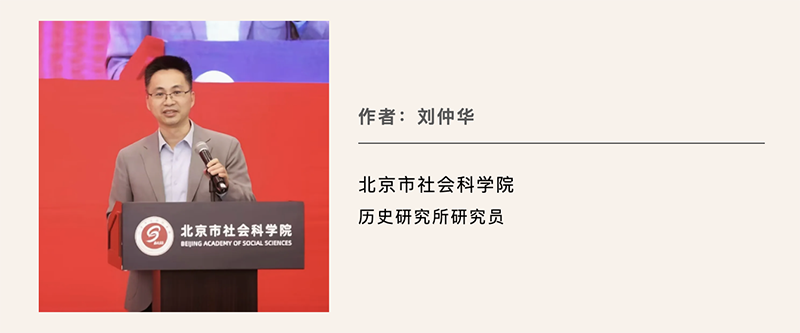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北京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悠久厚重、兼容并蓄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缩影,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特质的包容性。
包容性是北京历史发展的重要驱动
自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融合的第一次高峰,在这一时期,北京以蓟城为标志,成长为一个地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当时的蓟城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以齐、晋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与以山戎、孤竹等东胡民族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互相碰撞交融,最终孕育出兼具多元特征的燕蓟文化。
自秦汉至隋唐,是中华文明融合的第二次高峰,北京在此进程中完成了从蓟城到幽州的城市跃升,成长为华北区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北京地处广阳郡,蓟城是治所。汉代将蓟城视为巩固边防的战略要地,采取了加固长城、修建驰道、迁徙百姓实边等措施。东汉后期,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草原民族崛起,频繁入塞,区域格局随之生变:曹魏政权在蓟设立征北将军,辖幽州刺史和护乌桓、鲜卑校尉,开启了幽州作为多民族管理枢纽的序幕;此后历经西晋、十六国至北朝,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魏、东魏、北齐等政权先后更迭,匈奴、鲜卑、乌桓、氐人、柔然、突厥等民族在此地频繁活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堪称包容了多种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大熔炉,直到隋唐统一,这种不断积累的包容性历史积淀,奠定了隋唐时期幽州作为军事重镇、商业都会和交通中心的城市地位。
自辽、金至元、明、清,是中华文明融合的第三次高峰,在这一阶段,北京长期肩负历代王朝都城之重任,由北中国的政治中枢跃升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五代时期,后唐河东幽州节度使石敬瑭向契丹政权割让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随后契丹将幽州设为陪都,称"南京"。辽代陪都的设立,不仅改变了北京的城市性质、提升了城市地位,而且开启了北京长期作为王朝都城的历史。此后,金朝将北京升为中都,元朝以大都为全国首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守国门",清朝延续并完善了这一都城体系。可见,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的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推动着北京城市的不断发展。
包容性塑造了北京的城市文脉
辽金以来,包容多民族、多地域文化的历史资源对北京城市风貌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三山五园为例,这一区域作为都城苑囿功能区的开发和利用,始于辽、金两代。辽代在香山建香山寺。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建金山行宫。元代改金山为瓮山。进入清代后,基于大一统的文化建构和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融合,三山五园作为御园的建设达到高峰。为保持八旗骑射能力与军事战斗力,清朝统治者经常在京西御园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操演,如玉泉山大阅、畅春园阅武楼、香山演武厅、圆明园校射等活动。这些带有浓厚草原文化特色的军事活动,是无法在空间比较局促的紫禁城里进行的。可以说,正是由于皇帝在园居理政期间,为保持八旗骑射能力和军事战斗力的军事操演的需要,促成了三山五园等御园的形成与发展。
又如京杭大运河,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塑造北京城市文脉的典型载体。大运河是各地域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如同一张活力四射的网状大动脉,输送着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荆楚文化以及吴越文化的精髓,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这种交流既有北方与中原文化的南迁,也有江南文化对北方的影响。
大运河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通过联通东部沿海的五大水系,使得北京在融合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基础上,又吸纳了海洋文化。正如梁启超所言:"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京杭大运河堪称推动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国之重器"。
各宗教信仰在北京多元并存
北京多元信仰与宗教并存的格局,是在城市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其中,代表中华文明儒家信仰最核心的坛庙,在辽金以后尤其是元、明、清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礼制建设而逐渐成形,是北京多元信仰和宗教并存的底色,而且主要分布在象征礼制核心的中轴线上。其他散落在北京各处的庙宇,记录了各宗教信仰在北京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色,也展现了北京城市厚重的文脉。
辽、金、元三代,北京城市地位大幅提高,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统治者虽然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但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都非常重视宗教信仰的教化作用。史载,辽道宗"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辽圣宗时续刻房山云居寺石经,天庆十年修建天宁寺塔,位于阳台山麓的大觉寺也始建于辽代,时称"清水院"。金代统治者同样尊崇佛教,阜成门内大街的广济寺,南横西街的圣安寺,石景山的双泉寺都始建于金代。
元代统治者为巩固蒙、藏联合,以藏传佛教为国教,尊奉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今天位于阜成门内的妙应寺(俗称白塔寺),即是由国师八思巴推荐的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设计建造。
明代统治者延续儒、释、道并重的宗教政策,尤其道教获得快速发展。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迁都北平,尊崇真武大帝,在中轴线北端的万宁桥东侧兴建灵明显佑宫,又建灵济宫。嘉靖帝痴迷道教,兴建了御用道观大高玄殿。万历朝,李太后因出身宫女,为巩固地位,将自己塑造成菩萨转世,特别热衷佛事活动,万寿寺、长椿寺、慈寿寺等京城名刹,皆其所建。
进入清代,统治者为加强对蒙古地区和藏族地区的统治,积极强化藏传佛教这一文化纽带,在北京多处修建寺庙,供养蒙古和藏族喇嘛。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在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修建黄寺作为其驻锡之所。翌年,在黄寺旁又为五世达赖喇嘛修建了东黄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代国家统一最后完成,相应地,在北京修建佛寺的活动也达到了顶峰。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乾隆帝将原为雍正即位前的旧府邸雍和宫改为喇嘛庙,成为京城规格最高的藏传佛教寺院。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乾隆在南苑德寿寺接见六世班禅,又在香山建昭庙,作为班禅夏季驻锡之地。北京历史上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局面,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也促进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世界文化在北京兼收并蓄
中国地处东亚,四周虽然存在着诸如高原、沙漠、海洋等天然地理屏障,但古代中国始终以开放姿态接纳异域文化。辽、金之后,北京作为都城,更成为中外文明互鉴的场域。
元大都被誉为"世界之城",大都城内不仅有来自日本、高丽、安南、缅甸、暹罗的使臣穿梭,还有来自中亚、欧洲的旅行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前后抵达元大都,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任职并居住生活了17年之久。此后,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也曾游历元大都。
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来华,揭开了近代以来中西文明互鉴的序幕。相比于传教士所试图传播的宗教,他们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科技知识则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明朝末年,利玛窦一到北京,就向皇帝敬献了自鸣钟,万历皇帝很感兴趣,把玩不已。清前期,西洋钟表、音乐、油画在宫中颇受欢迎。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等人,不但向康熙帝进献西洋乐器,还会为他讲解西洋乐理及演奏技巧。
清前期的北京对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做到了兼收并蓄。康、雍、乾时期,围绕新旧历法之争、《律历渊源》等书籍的编纂、北京观象台的改造、天文观测仪器的制作以及全国舆图的测绘,不仅涌现出了众多钻研历算学的博学之士,如王锡阐、梅文鼎、江永、戴震等人,而且以何国宗、梅瑴成、明安图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与西方传教士碰撞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清代天文历算等科技知识的传播。直到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时,纂修官不仅肯定了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历算学知识,而且也直接收录了不少传教士的相关著述,如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等著作都在其中。
综上,北京作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典范,其发展历程展现了文化融合的深层逻辑与实践智慧。这种包容性超越了简单的文化叠加,形成了具有创新特质的有机融合模式。从历史维度看,北京的文化特质源于三个关键层面的互动:在多民族交往中实现了文化基因的重组,在多地域交流中实现了文化创新力的迭代,在文明互鉴中促成了价值理念的升华。这座城市既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点,也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连接线,更是传统智慧与现代创新的结合部。这种融合创新的实践表明,文化包容的本质在于将差异转化为发展动能。北京的经验揭示,文明的生命力既需要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更需要建立创造性转化的机制。正是通过这种动态平衡,中华文明方能持续焕发新的活力,在世界文明谱系中展现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