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英语世界讲述:中国社区治理和公民参与的新理论和新经验
——从英文专著《走向民主化社区》的出版谈开去
书是文化沟通的一个窗口
从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视野望去,一本讨论本土社区的专著很像是一张游览图、一个窗口,而研究者则像是一位导游,向纷至沓来的世界各地的读者热情地介绍本地的社会生活和风土民情。当笔者用英文撰写的学术专著《走向民主化社区——中国城市自下而上公民参与的兴起》(Towards Democratic Neighborhoods: The Emergence of Bottom-up Citizen Engagement in Urban China),由德国兰伯特学术出版社出版时,在欣喜地看到辛勤耕耘所带来的一份收获之余,笔者更由衷地感到作为“导游”的一份责任和向英语读者谈论中国发展、推介中国经验所带来的一份畅快。
道理很明显,本书向英语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来展示当今中国社区的变化,它除了在德国发行,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发行。按照兰伯特学术出版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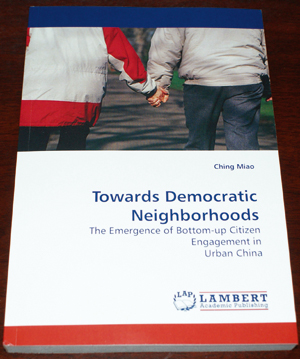 的介绍,它的图书产品是经由在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十几家大型网上批发书站,与全球80000家书店和3000家网上书店发生联系。
的介绍,它的图书产品是经由在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十几家大型网上批发书站,与全球80000家书店和3000家网上书店发生联系。
《走向民主化社区》一书是笔者向英语世界较为系统地推介中国公民参与和社区治理新理论和新经验, 彰显中国影响力的最新努力之一。在这方面,国外文献对此的了解相当滞后。记得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博士研究时,查阅了有关当今中国社区的英文资料,尽管可以找到少量中外学者的英文论文,但在号称北美最大图书馆之一的多大图书馆,想找一本中国学者用英文撰写的当今中国社区的专著却并非易事。所能借到的是费孝通的英文版的《乡土中国》,书中有不少下划线和着重号,可见借阅者不少。顺便提一句,在北美借阅的图书经常看到有下划线和着重号,这大概是得益于那里的图书馆比较看重图书的价值不在于“藏”, 而在于“用”——不断地在读者手中流通。
当然,在国外阅读《乡土中国》的英译本仍然别有一番感受。不过,它所讨论的毕竟是昨天的社区故事——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社区的状况。而对于快速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来说,它的社区变化,特别是城市社区治理和公民参与的新发展和新观点,显然需要当代中国学者社团的努力,作为导游向世界多方位地讲述中国社区发展的新故事。
彰显中国文化对公民知识传统的贡献
本书分析了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新现象——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包括社区直选、权利话语以及社区自治章程的制定等。本书深入讨论了新价值是如何兴起的,以及推动其发展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因素。研究采用了多层面分析的方法,结合了社会文化分析和经验研究,包括展示了北京若干社区的居民问卷调查的一些结果。
研究表明,与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治理的话语相比照,就整体构架而言新价值是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经验数据显示,诸如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居民所置身的社区结构等因素影响着个人是否卷入自下而上的参与活动。人们对公民参与的选择和理性自觉有一个渐进的和累积的过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房产所有者,以及市场化城市化和社区自治等因素,并有机会到公民参与业已常见的地方去旅行,走向民主化社区的本土资源正在不断增长。
本书的结尾,笔者在总结了中国社区发展和公民参与的一些特点后指出:“在本研究开始时,我相当好奇于下述问题,什么叫做独立的公民以及什么是中国语境中的公民参与?是否当一个人有了一次经历,例如读了一本西方学者有关公民权或者公民社会的书,或者参加了一次志愿者的活动,他/她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公民?本书的社会文化分析和经验研究帮助我找到了一种解答:在社区活动中有关公民参与的理性自觉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历经了人的行为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互动。”
笔者还向英语读者给出了一个中国社区参与的很本土化和生活化的评论:“有关参与的故事在中国城市的不少商品楼社区正在发生着。当那些被称为“社会人”的人(他们之中有很多有着大学以上的学历)搬进商品楼,面对种种问题需要同物业公司与政府来协商,他们不能不志愿地携起手来推进共同的利益和维护自身的权利,不能不建立规则来培育居民间的信任。
无论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用什么词来描述这种参与,诸如公民社会角色或者公民社会组织等,我所理解的公民参与指涉了遵循契约和透明的规则来建立参与网络,指涉了人们发展新的社会资本包括在社区的正式和的非正式的组织,以及有利于自下而上和平等参与的话语。”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一个民主化导向的社区意味着一个过程,即人们如何调试他们的本土文化来发展公民社会和社区组织。这一参与的过程真实地展现了人们如何创造他们自身的生活以及实现他们的福祉。”
很明显本书在阐发中国公民参与的一条主线是着眼于本土资源,从社会生活和中国文化的语境、从人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来展开什么是公民的讨论,这就将中国公民文化的发展放在了一个稳妥的基础上,避免了局限于西方中心论的视角讨论公民主题所带来的困境:公民解说成了对西方历史成就和概念的脚注,既难以解释中国社区的现实生活也难以用来解决问题。
不仅如此,本书以及笔者正在撰写的第二部有关中国公民文化的专著也一直在坚守这样的观点,很有必要纠正国人有关公民教育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公民文化纯粹是一种舶来品和外来文化。对此,笔者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专访时作了澄清:您觉得东西方文明哪个更加适用于公民文化,我们的文化中哪些是有利于这一建设,中国应该如何扬长避短?我谈到:“首先应当强调,中国文化对于公民知识传统有着自己的贡献,即便在古典治理思想中也并非白纸一张。例如,在先秦时代中国思想家就提出了‘民为邦本’‘无为而治’等思想,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已经有一些研究和证据表明这些思想对后来欧洲的启蒙运动有启发。这些思想强调基层自治,认为善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少干预,这对今天中国公民文化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实际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我想这里面有传统的印迹。”
互联网的广阔平台:活跃的学术出版和长尾理论
随着中国软实力的增长,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出版自己的英文专著来介绍中国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为此,围绕着本书的出版来谈谈国外学术出版的一些新特点或许是有帮助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兰伯特学术出版社的宗旨,它公开承诺专注于出版各类学术专著包括博士和硕士论文。尽管被选中的作品既有着学术的也有市场的考量(出版社有评审委员会来负责此事),这种专注于推出学术著作的取向以及出版社主动联系作者的活跃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出版公司搜寻作者的过程很像猎头公司的做法,不是坐等作者上门,而是主动寻猎来网罗好的研究文献。本书的洽商就是从兰伯特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主动发来电子邮件启动的。
又例如,兰伯特出版社在互联网平台上有一个两万名作者的数据库,存有作者的研究领域和联系方式,而且每一个作者都有这样一栏“请您推荐”,回报是一旦所推荐的书能够出版,推荐者将会得到一本赠书。由此可见,在推动学术专著出版以及主动与各领域学者互动方面,国内出版业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本书的出版,从洽商到签约出书都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进行,其便利程度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洽商出版的过程中,从编辑邀约出书,笔者提交电子版的学术专著送审,到版式设计、封面选择、一些有关作者权利的讨论以及合同条款的确认等,互联网提供了便利的渠道。经过十几个回合的电子邮件交往,虽然编辑和作者都未谋面,由于双方都信守承诺,因而在相当轻松的氛围中,书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出版了。这也说明通过互联网平台,在一个有序、守信和相互尊重的氛围中出书,作者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交往成本。
与此同时,兰伯特学术出版社专注于经营学术著作也不能不使人想到一个的问题,这样的专营学术产品之道能否持续地运转下去?深入地探讨已非本文所及,不过其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例如,使用兼职编辑、运用PDF软件的轻印刷以及零库存的运营等,都是减低成本之道。此外,互联网所带来的长尾效应:即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的产品占据的市场份额就可以和那些热卖品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由此可见,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为学术书籍提供了能够持续销售的常销书市场。大约也正是看到了长尾效应,兰伯特学术出版社的知识产品经由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大型网上批发书站,与全球80000家书店和3000家网上书店发生联系,这就使得出版商可以找到那些以往被遗忘的角落。以上种种,笔者以为都是国内有关学术出版业界值得思考的。
让中国学者的英文著作多起来:转换不发达心态和制度激励
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当中国读者走进书店和图书馆,各个学科的国外著作的中译本已经成了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相比之下,在国外的书店和大学图书馆中,中国学者的英文版著作却难得一见,这一反差也说明了中国需要推进软实力的迫切性。因而,如果将笔者英文版专著的出版置放到中国影响力扩展的大背景下去讨论,其关注点自然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需要看到英语世界的需求, 看到国外读者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是相当感兴趣的,这当然与近些年来中国的快速增长有关。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因素,《走向民主化社区》一书在商讨出版期间,有不只一家国外出版社来电子邮件主动洽商,这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国外学术界和读者希望看到中国学者作为亲历者来讲述中国发展的故事和中国模式。
另一方面更需要看到,在中国国力日升的过程中,作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国需要在国际讲坛上大力推介其发展的理论和经验,需要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使用英文写书出书来讲述中国故事无疑是重要一环。而且,中国学者社团中已经并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既然渠道和能力已经并正在拓展,那么让中国学者的英文著述多起来的关键就在于转换不发达心态和适当的制度激励。所谓不发达心态不外是指重视硬实力而忽视软实力,看不到中国人使用英文写书的能力以及不断拓展的出版渠道等,以为这些事都是遥不可及的。
强调制度激励,就是让更多的中国学者用外文写书出书得到支持和鼓励,包括资金支持和成果评价机制。道理很简单,一个中国学者使用英文著书立说,要让人家看得明白并且能够邀约出书,其难度和所耗费的精力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对这样的勤奋缺乏制度激励,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去做这类事倍而功半的“傻事”,这当然对彰显国家软实力不利。
就成本-效益而言,对国人出版英文专著缺乏制度激励也是短视之举。试想从中学到大学乃至研究生,有那么多的人花费了那么多的资金和精力来学习外语,而且在职场上又有各种各样的外语考核包括高级职称考试等制度举措。然而,当多路助攻的球已经到了大门口,恰恰是在“临门一脚”的关口——需要日益增多的中国人能够面向英语世界著书和讲演,这些最能展现英语学习成果的环节和有效展现中国软实力的领域——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对射门的激励却没有了,这岂不是功亏一篑?!
向英语世界讲述中国发展的故事:软实力增长的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无非是在说明,当渠道和能力已经开始具备,加上观念更新和制度激励,要看到在国外的书店、大学图书馆和网上书站,各个学科的中国学者的英文著作能够多起来并非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同时,将英文著书和软实力联接起来的一个更为深层的理由还在于,当日益强盛的中国希望世界能够更加客观地和公正地看待其发展,在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我们除了需要一些国外学者和国外媒体的声音,更为宽广的和主动的渠道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使用外文来多方位地讲述中国故事,帮助世界来了解中国。
很可能也正是看到了这一潮流所向,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明确将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的规范的英文著述视为高等级的学术成果,这一制度设计是推进中国软实力增长的应有之义。当然,要持续地激励更多的中国学者进入这一领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包括国内出版商的积极参与以及系列化的制度激励。
不仅如此,随着在国外的书店、图书馆、网上书站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外文著作来多层次、多学科的展示中国的发展,其浩荡的潮流所向,人们不时听到的几个诋毁中国的声音,也就不足为虑了。
总而言之,笔者高兴地看到《走向民主化社区》一书的出版不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成果库增添了新的一页,而且能够为促进文化沟通和推进中国影响力作出一点贡献。笔者也乐见,循着本文建议的方向去努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能够出版自己的外文学术专著并使之成为国际交流中的常见之事,这应当说也是中国软实力增长的应有之义。


